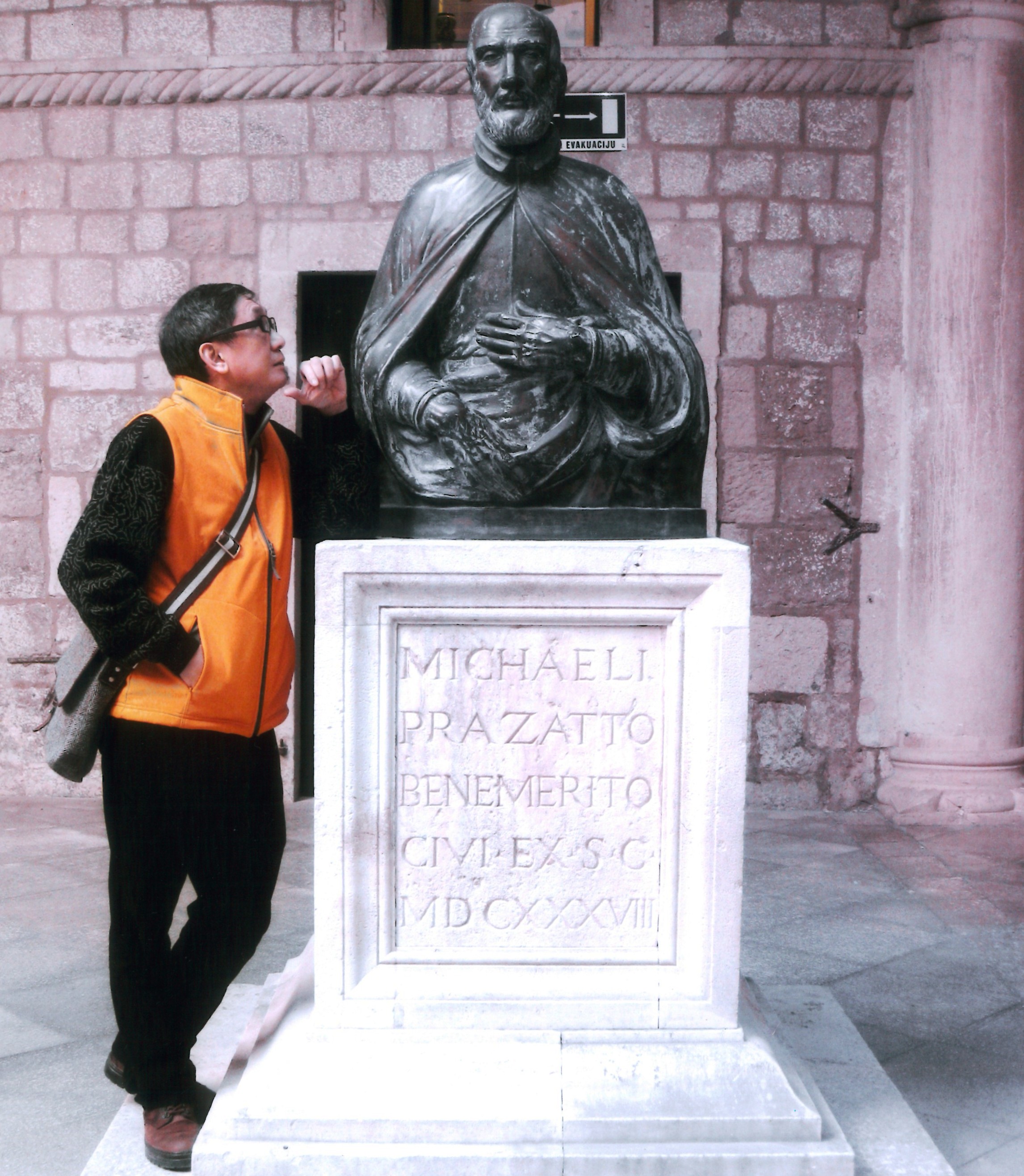我們的馬Sir,馬老師,馬教授,是我們一個親和,嚴肅,天真,同時也是感性的師長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這裡轉貼黃兆瑜師姐對初次瀏覽本站的意見。多謝黃師姐鼓勵。
馬 Sir 的網頁設計精簡,內容豐富,實在目不暇給。其藝術作品也有多方之立意,意奇則奇、意高則高、意遠則遠、意深則深、意新則新、意古則古,千變萬化,別具風格,不落前人窠臼。篆刻題材多樣,字畫之間,寬能走馬,密不容針,奇趣橫生;書法則各體皆備,楷隸大方穩重,行草則如行雲流水,篆書則古樸之外,別有生趣;國畫方面,馬Sir可以說已能將技術、文化、哲學共冶於一爐,筆法、佈局、色彩都能運用自如,不著雕琢痕跡;其鍾馗圖系列也題材各異,人物衣著、神情、形態亦各有千秋,可稱一絕。欣賞馬 Sir 的水彩畫,就可以知道他在控制水份、調色、刻劃線條方面已達得心應手之境界,鳥類畫系列更顯得其觀察入微,否則不能每隻鳥兒都畫得形神兼備。在此期待馬 Sir 上載更多作品,特別是版畫和攝影的大作,大飽觀眾的眼福!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馬桂綿老師是我的啟蒙老師。還記得中一第一堂美術馬老師的模樣,他說話的神緒,以及如何由此愛上美術。
馬老師讓我們懂得欣賞如何用一條線也可成畫 , 這個去繁從簡的概念其實擴闊了我的視野。 因為馬老師 ,我知道所描繪的圖像與周邊的線條以及畫紙四邊之間的每一個角落 , 其實都是畫 , 要正反呼應才達到一個有美感的構圖 ,這個正反合一的概念對一個中一生來說,不是啟蒙是甚麼? 還有線條的美感,從一條線到中國文字,以至書法,不同字體中,從粗幼間 , 線條發揮出來的那種美,簡直是震撼的。
亦因為馬老師, 我有自己對美的定義。而因為這樣 , 我會自信地 , 不盲目追上潮流 , 亦不隨波逐流 , 所以 , 我一次也未穿過當時流行的鬆糕鞋。 我會懂得色彩的配搭,我會喜歡簡約,我會傾向低調,因為我知道這樣較為配合我的性格。我也懂得欣賞別人獨突而誇張的裝束,而當中亦能看到誰是高手。只是這一點,就夠我活得精彩,因為每個人都是一幅行走著的畫。
所以我說,馬桂綿老師是我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視覺與審美觀的啟蒙老師。 亦因為馬老師,我知道怎樣才是一個好老師。在課堂上,至今,他是我見過最好的一位老師,無人能及,他是第一亦是唯一。
勞燕芬 銘賢(1976年畢業生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1971年九月六日下午,在香港九龍石硤尾的的一所英文書院四樓,一班十三歲的小孩開始他們初上中學的第一堂美術課。才開課幾天,同學們互相還沒怎麼認識,課堂鴉雀無聲。有話聲響起,孩子們聽到美術科老師的第一句話:「我是不會畫任何範本給你們臨摹的!」說此話的是個二十來歲,十分清秀,白臉書生形的大哥哥。
本文也會於一段時間之後換上老師的其他弟子,講講他們對老師的敬慕之情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《燃藜集》序
《燃藜集》所收的是過去四十年的舊作。
幾年前,因為搬家,偶從雜物中發現了一些書畫和詩稿的斷簡殘篇,還有印章千多方,都是四十年來不同時期的舊作,心情就好像重見久別了的兒時玩伴,既親切又陌生,心想這些「心血」丟失了怪可惜,一時糊塗,迷了心竅,就決定在這些自珍的蔽帚中選取部分來結集出版,聊作人生旅途上一段鴻爪的印記。
年來苦於為稻粱謀而奔波,雜務紛繁,編印工作也就一拖再拖。有時翻看稿件,見到那些難登大雅的東西,實在也有點替自己難過。曾經好幾次想放棄,但由於不時得到一些師友的勖勉,終能在數年後的今天奮其餘勇,付之剞劂。最感慶幸的是得到杜祖貽教授、王韶生教授和靳埭強先生分別為這三本結集賜序,又得劉小康兄為整套集子作了設計,相信這些就是整套集子最值得一看的地方了。
《燃藜集》由結集以至出版,拖延了好幾年,當年錯愛我和鼓勵我出版這本集子的師友中,有好幾位惜已作古,未能目睹它的面世,愧悔之餘,也只能聊效季扎掛劍了。
《晉書‧阮籍傳》裏記其兄子阮咸,說「七月七日,北阮盛曬衣服,皆錦衣燦目。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,人或怪之,答曰:『未能免俗,聊復爾耳!』」。別人晾曬的衣物都是燦目錦綺,家貧沒有甚麼好衣物可曬的,只好掛粗布短褲,算是不能免俗,姑且如此而已。這本《燃藜集》的出版,也可算是「未能免俗,聊復爾耳」,大雅方家,也就不要見笑了吧!是為序。
馬桂綿於二零零二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