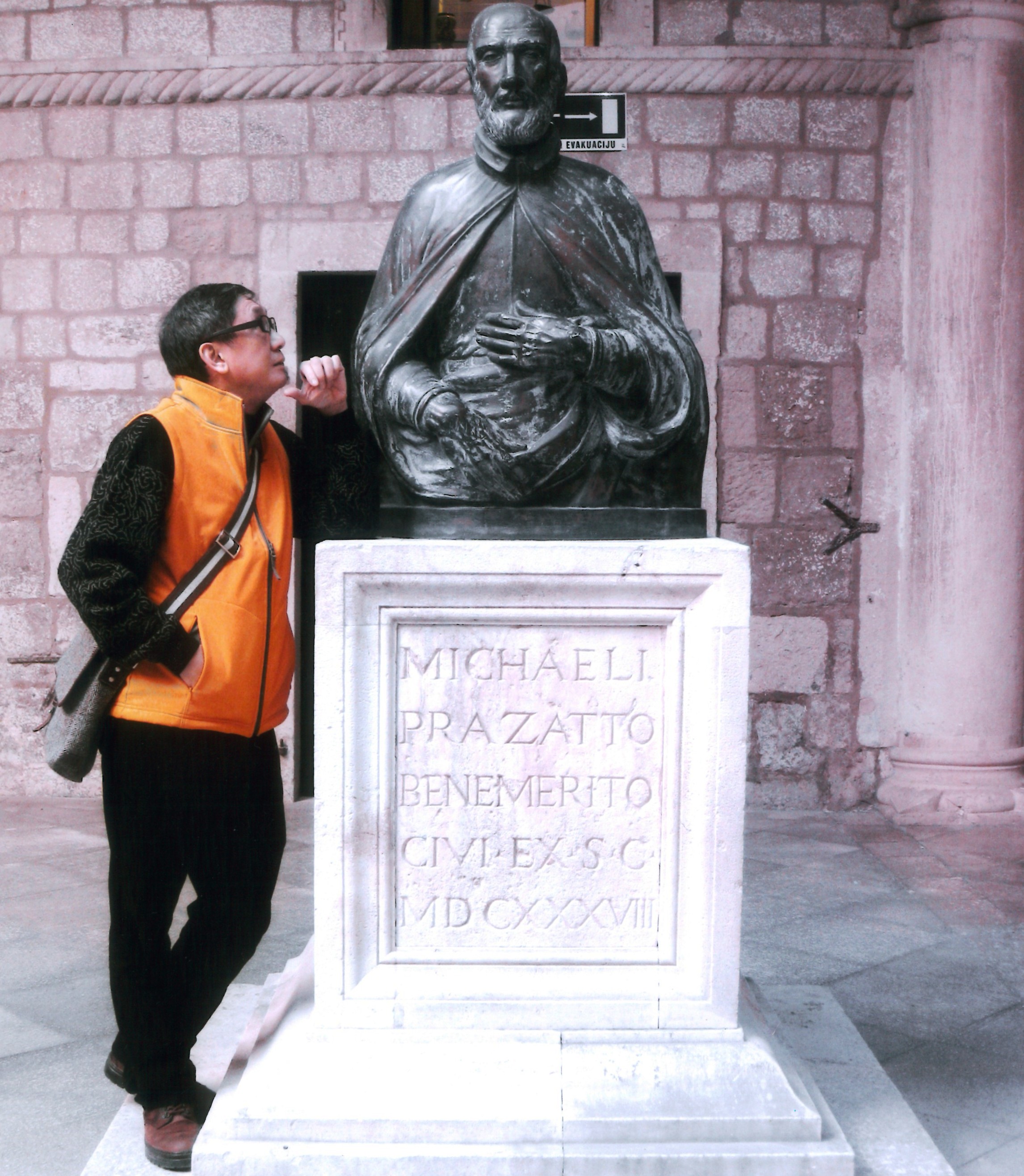我们的马Sir,马老师,马教授,是我们一个亲和,严肃,天真,同时也是感性的师长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这里转贴黄兆瑜师姐对初次浏览本站的意见。多谢黄师姐鼓励。
马 Sir 的网页设计精简,内容丰富,实在目不暇给。其艺术作品也有多方之立意,意奇则奇、意高则高、意远则远、意深则深、意新则新、意古则古,千变万化,别具风格,不落前人窠臼。篆刻题材多样,字画之间,宽能走马,密不容针,奇趣横生;书法则各体皆备,楷隶大方稳重,行草则如行云流水,篆书则古朴之外,别有生趣;国画方面,马Sir可以说已能将技术、文化、哲学共冶于一炉,笔法、布局、色彩都能运用自如,不着雕琢痕迹;其钟馗图系列也题材各异,人物衣着、神情、形态亦各有千秋,可称一绝。欣赏马 Sir 的水彩画,就可以知道他在控制水份、调色、刻划线条方面已达得心应手之境界,鸟类画系列更显得其观察入微,否则不能每只鸟儿都画得形神兼备。在此期待马 Sir 上载更多作品,特别是版画和摄影的大作,大饱观众的眼福!
2020年7月18日 铭贤校友 黄兆瑜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从一字说起
马桂绵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。还记得中一第一堂美术马老师的模样,他说话的神绪,以及如何由此爱上美术。
马老师让我们懂得欣赏如何用一条线也可成画 , 这个去繁从简的概念其实扩阔了我的视野。 因为马老师 ,我知道所描绘的图像与周边的线条以及画纸四边之间的每一个角落 , 其实都是画 , 要正反呼应才达到一个有美感的构图 ,这个正反合一的概念对一个中一生来说,不是启蒙是甚麽? 还有线条的美感,从一条线到中国文字,以至书法,不同字体中,从粗幼间 , 线条发挥出来的那种美,简直是震撼的。
亦因为马老师, 我有自己对美的定义。而因为这样 , 我会自信地 , 不盲目追上潮流 , 亦不随波逐流 , 所以 , 我一次也未穿过当时流行的鬆糕鞋。 我会懂得色彩的配搭,我会喜欢简约,我会倾向低调,因为我知道这样较为配合我的性格。我也懂得欣赏别人独突而夸张的装束,而当中亦能看到谁是高手。只是这一点,就够我活得精彩,因为每个人都是一幅行走着的画。
所以我说,马桂绵老师是我第一位亦是唯一一位视觉与审美观的启蒙老师。 亦因为马老师,我知道怎样才是一个好老师。在课堂上,至今,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老师,无人能及,他是第一亦是唯一。
劳燕芬 铭贤(1976年毕业生)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1971年九月六日下午,在香港九龙石硖尾的的一所英文书院四楼,一班十三岁的小孩开始他们初上中学的第一堂美术课。才开课几天,同学们互相还没怎么认识,课堂鸦雀无声。有话声响起,孩子们听到美术科老师的第一句话:「我是不会画任何範本给你们临摹的!」说此话的是个二十来岁,十分清秀,白脸书生形的大哥哥。
他就是我敬爱的马桂绵老师,带领我进入视觉艺术世界的牧者。
马老师除了是中学教师,也曾经是跨国出版集团的高层,也是玩票的专业平面设计师,书画家。他的作品不时出现于某消费品包装,或某活动的广告,甚至国内旅游景点地名标志,却低调得没人认识。今天,一般人多用博士或教授称呼他,因为马教授在出版界退休后仍在大学的中文系当教授。这个网站目标是把老师的创作公开展示,不认识老师的朋友想多了解,可以网上搜寻。不是网主懒惰,实在是老师多次严训不要用此站帮他老人家卖广告。
老师常自嘲:「吾不为五斗米折腰,却为了两千石折了腰!」老师并非看不起五斗米那么少而把价钱提高。两千石所指的是他刻了两千多方图章,而主要都是石章。搬家时,因为搬他的宝贝篆刻作品而导致腰疼呀!所有可以理解老师可能最自豪是他的篆刻。
老师过去为自己出版过三辑燃藜集,收录了他的书法,国画及西洋画;付梓成书后全部免费送给朋友和学生。他原意要再出版第四集,但从过去经验因为纸本印刷的实体画册流通和发行量都不多,不广;无法让老师的众多弟子粉丝分享。网主就提议不如搞个网站把老师作品于网络展示于世。 这是网主首次搞网站,可能比较粗糙。希望不善之处能够慢慢改进。
本文也会于一段时间之后换上老师的其他弟子,讲讲他们对老师的敬慕之情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《燃藜集》序
《燃藜集》所收的是过去四十年的旧作。
几年前,因为搬家,偶从杂物中发现了一些书画和诗稿的断简残篇,还有印章千多方,都是四十年来不同时期的旧作,心情就好像重见久别了的儿时玩伴,既亲切又陌生,心想这些「心血」丢失了怪可惜,一时糊涂,迷了心窍,就决定在这些自珍的蔽帚中选取部分来结集出版,聊作人生旅途上一段鸿爪的印记。
年来苦于为稻粱谋而奔波,杂务纷繁,编印工作也就一拖再拖。有时翻看稿件,见到那些难登大雅的东西,实在也有点替自己难过。曾经好几次想放弃,但由于不时得到一些师友的勖勉,终能在数年后的今天奋其馀勇,付之剞劂。最感庆幸的是得到杜祖贻教授、王韶生教授和靳埭强先生分别为这三本结集赐序,又得刘小康兄为整套集子作了设计,相信这些就是整套集子最值得一看的地方了。
《燃藜集》由结集以至出版,拖延了好几年,当年错爱我和鼓励我出版这本集子的师友中,有好几位惜已作古,未能目睹它的面世,愧悔之馀,也只能聊效季扎挂剑了。
《晋书‧阮籍传》里记其兄子阮咸,说「七月七日,北阮盛晒衣服,皆锦衣灿目。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,人或怪之,答曰:『未能免俗,聊复尔耳!』」。别人晾晒的衣物都是灿目锦绮,家贫没有甚麽好衣物可晒的,只好挂粗布短裤,算是不能免俗,姑且如此而已。这本《燃藜集》的出版,也可算是「未能免俗,聊复尔耳」,大雅方家,也就不要见笑了吧!是为序。
马桂绵于二零零二年